五專二、三年級,在某次話劇排練中想要來個賺人熱淚的橋段,所以雙膝大力的跪在木造地板上,想要營造出假悲情,雖然之後沒有納入劇情且全程就只有那一下,但膝蓋就有明顯的痛感且瘀青,但當時不以為意,心想瘀青應該幾天就會好,所以也照舊跑跳和上體育課,直到有天跳著搶籃板後落地的那霎那,覺得左膝好像傷到,之後就明顯感受那疼痛感一直都存在,而到有天發現,左腳已經無法打直時才發覺事態嚴重,之後到醫院經過一連串的檢查,終於得知這長久疼痛的原因『外側半月板部分破裂和十字韌帶部分斷裂』,醫生建議要動個小手術,因為要把破碎的部分清乾淨,才能解決腿打不直的問題。
經歷過國小三年級的初體驗後,對手術沒什麼懼怕,反正最痛的就只是挨那一針罷了,何況這次只是把碎掉的東西清乾淨,就像吃螃蟹時用小叉子把螯裡的肉挖乾淨一樣簡單,根本是piece of crab! 但記得嗎? 上次因為年紀小,擔心我會害怕所以全身麻醉,可是這次不同,畢竟也虛長幾歲,而且只是"小手術",所以醫生建議半身麻醉(全身麻醉對身體還是比較不好),但同時也被告知,半身麻醉是要在脊椎附近挨上一針,會蠻痛的,但我想就是個"小手術"而以沒在怕的啦,所以同意半身麻醉,開刀前一天先住進醫院做些例行的檢查&開刀前都必需禁食(這比較要我的命),等到隔天換上護士送來的藍色的手術衣、插上點滴的針後重頭戲才算真的開始(拉紅幕ing)。
從病床換到剛剛好只有一個人寬且冷冰冰的手術檯,深怕一個沒躺好就摔下檯,這次手術室裡醫生好多,有些是來見習吧?! 說實在,躺在那被那麼多人看還真尷尬,所以只好兩眼呆呆的看著天花板,當時醫生們和護士間的對話我也不在意,直到有人請我側躺,要準備打半身麻醉針才又回過神。真的,打在背部真的不痛,雖然在施打前護士一直叫我不要緊張及深呼吸,但這比插點滴的針真的不算什麼,所以這唯一讓我緊張的部分就輕輕鬆鬆的過了。
在等藥效發揮的時間裡,依然凝視著天花板,突然有位醫生移了台電視到身邊,當下想『哇,那麼好,還可以看電視打發時間呀!』結果他竟然說,這電視是為了讓我看手術過程的(是因為打針連唉都沒唉一聲所以覺得我很勇嗎?!),我的天....這是哪門貼心的服務? 當然,如果不想看是可以不必看的,但依我這個俗辣個性,當下也沒拒絕 ,又過了一陣子,麻醉師來測試麻醉藥發揮的程度,他先輕捏我的手臂再捏大腿,由這兩邊痛感的落差來判斷,麻醉藥當然有發揮效果,大腿的痛就像離大腦幾萬光年一樣,看他明明就捏著,但經像是接上電話線的網路傳輸速度,遲鈍的告知我『痛』。
測試完沒多久後,被告知要在左大腿綁止血帶,且在綁緊的過程會有點痛。『止血帶』顧名思義是拿來止血用,這一切是多麼符和常理,但殊不知,原來它也可以當殺人武器,雖然它沒有『折凳』一樣可便利攜帶、藏於民居而不被人察覺的大殺傷力兇器,但在手術室裡,它折磨人的成度絕對能和折凳相抗衡。當時沒仔細看清楚止血帶本人的模樣,但它帶來的痛,老娘這一輩子不會忘記。剛套上時就蠻緊的,但為了把功能展現到淋漓盡致,不知道哪位天殺是醫生還是護士,瘋狂拉緊止血帶本人,那何止"有點痛",根本是天殺的有夠痛,綁那麼緊根本是要我的大腿直接壞死、截肢吧,當時只有一個念頭『乾脆把它套在脖子上,勒死我算了,這還不用費你那麼大的力氣。』雖然心裡這麼想,但或許這就是醫師在"行刑"告知的目的,他已經先警告我會"有點痛"了,所以我天真的把這一切視為"正常",就此後我就用"正常的"的態度面接下來的手術。(寫到這左膝也開始痛了起來)
綁好止血帶之後,麻醉師就坐在左手邊我視線看的到的椅子上,手術室裡又忙了一陣,突然大腦接收到膝蓋那傳來一連串要命的感覺,雖然有麻醉藥幫忙,感覺是有比較遲鈍,但當膝蓋是被不知明的東西劃一刀,那個痛是沒有半點遲疑的告訴大腦說『這...真的很痛。』雖然如此,我還是用不知道哪來的"相信專業"和這一切都是"正常的"態度來面對,所以這一刀我。忍。住。了。
接下來,醫生在剛劃開的地方插入一個無止盡的醫療器具。說它無止盡,因為它帶給我是持續、不間斷的痛(快噴淚了我),當那未知的器具插入膝蓋時,我用雙手頂著手術檯的檯面,用盡吃奶的力氣試著移動我那半麻醉的下半身,試圖逃離這地獄般的折磨。我當時真的有移動身體,但醫生們似乎沒有發現, 我心想『這是正常的嗎?? 這麼痛是正常的嗎??』,就在還沒想清楚前,第二次開始了,這次感覺它不只是插入腿裡,而是直接插入我的腦袋一樣,當時眼裡已經含著淚、眼睛瞪大、頭上冒著冷汗且咬緊牙根,但我就像是一頭自己送上門的牲畜一樣,被五花大綁且任人宰割,這次我真的好想破口大罵,隨便拿把手術刀自我了斷。
當痛楚尚未結束前,我強忍住眼眶裡的淚水,將頭轉向坐在椅子上邊看世界電影雜誌的麻醉師問『我現在還有感覺,是正常的嗎?』就這句讓他從椅子上跳起來,並且一臉不可思議的問『妳還有感覺?』,我像沒了魂似的回了他『是的。』,再來就聽他果斷的提出"全身麻醉"的提議,當下只能微微的回一個字『好』,心想,反正已經死過一次,要怎樣我都無所謂了。
當時已被痛覺侵蝕且全身發冷的我,永遠忘不了戴上全身麻醉的呼吸罩和地獄告別的那一幕。視線的左邊是麻醉師,右上角是那台還沒開的電視,我用力吸著呼吸罩裡送來的氣體,希望它能趕緊帶我離開這裡,即始閉眼後再也睜不開也罷。半閉時,在眼眶打轉以久的眼淚終於經由眼角滑落到耳朵(到現在還記得那顆眼淚的溫度),而同時嘴裡冒出一聲小小聲的『Shit!』,就一滴淚和一句髒話帶我離開這人間煉獄。
唉,回頭想想,這一切最不正常的人就。是。我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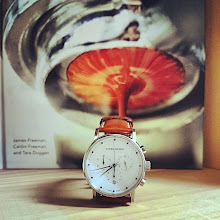



2 comments:
痛要勇敢的說出來!
Post a Comment